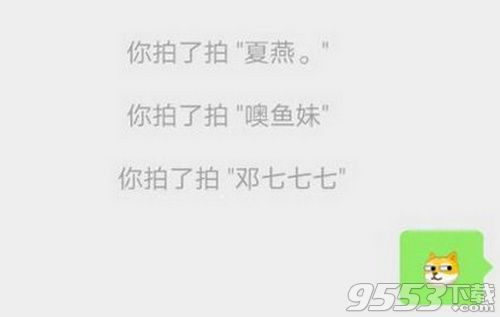作为“症候”的失语:青年电影人在时代与自我之间
创作是自由的,纵观电影史,各类风格和题材的电影都有佳作,但任何私人生活都嫁接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创作者也需要有做出有效表达的勇气。
文 / 特约撰稿 叶倩雯 发自西宁
第15届FIRST青年电影展结束一段时间了,关于它的讨论依然在发酵中。在翻阅征片报道的过程中,我很惊讶地发现参赛的作者中“90后”已经占到了六成,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世代渐渐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中坚力量。
在普遍的期待里,这群与中国经济腾飞一起成长,经受全球化与网络文化洗礼的青年导演应该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影像表达。但就在电影展结束后不久,一篇以“关注自己、逃避现实、放弃思考”为题目的文章就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文章通过对影展策展人段炼的采访,得出了如上对青年电影的判断,起到了某种警示作用。
有青年作者对此感到不服甚至委屈,“年轻人的电影就一定要表现社会问题,不能展现个人生活吗?”曾有作者向我当面提出这个问题。创作是自由的,纵观电影史,各类风格和题材的电影都有佳作,但任何私人生活都嫁接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创作者也需要有做出有效表达的勇气。
自恋、沉溺、逃避或许只是当下青年电影创作问题的表征,当我观看了今年入围的大部分作品后,首先感到的是表达的匮乏和退让,面对越发激烈的社会现场,年轻作者在时代与自我之间、公共与私人的夹缝里,呈现出一种普遍的失语状态。
无声的底层
关怀和关注底层与边缘人群,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青年电影作者的一个重要母题,一部分导演正是通过对边缘人群生命经验的书写替代了身体意义的社会实践,展现出某种套路性的创作倾向。底层的生活往往作为一种电影景观出现,鲜少有作品可以触及个体生命的真实痛感。
从这个维度来说,今年获得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两项大奖的电影《最后的告别》可谓难得,曾在北京电影学院一边做保安一边读书的导演张中臣极力将自己的真实经验与艺术电影的语法相结合,他试图通过一个聋哑保安方圆的眼睛揭示出一个乡村家庭三代人的普遍性遭遇。
▲《最后的告别》
方圆的身世很凄惨,是天生的聋哑人,民办教师父亲对他颇为嫌弃,后来又和母亲生了妹妹。谁知家庭遭遇一系列的变故:妹妹不慎掉进井里淹死;父亲在失去工作后又遭到巨大打击,精神出了问题;母亲最终选择离家出走……方圆只能和爷爷相依为命,在寂寞中长大,成为一家工厂的保安,日日看着监控镜头过活,直到父亲在医院杀人的消息传来……
应该说,《最后的告别》是一部悲剧浓度很高的作品,灵感来源于张中臣童年的往事,村里的大人患有精神疾病,为了一块手表杀害了家人……看得出来导演在方圆身上赋予了颇有野心的隐喻性,电影多次以电视新闻作为画外音,点出了大时代的变化,也提示我们在方圆听不见的外部世界,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左右人们的命运。方圆的职业因此变得重要,监控镜头是这部电影不可忽视的题眼,作为身在监控背后的人,方圆看似对一切了如指掌,其实却对现实无能为力,他无法介入其中,听不到也讲不出。
据说张中臣塑造聋哑人的形象并非偶然,这个角色有着真实的生活原型,但显然方圆的失语显示出某种底层的处境,他们总是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被剥夺了行动的可能性。换句话中,这同样形成了对当下电影创作的一种隐喻,通过无孔不入的网络,青年作者可以如同观看监控一样观看苦难的现实,甚至描摹现实,却无法真正把握现实。
无独有偶,获得“评委会特别荣誉奖”的香港导演李骏硕的作品《浊水漂流》里也有一个“失语”的年轻人角色木仔,这个人物虽不是主角,却可以看作全片的一个灵魂人物。电影的灵感来自于导演从事新闻工作时所遇到的一桩真实案件:2012年,香港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进行街头清扫工作的时候将一些“露宿者”的私人物品做了没收丢弃处理,随之引发了一系列的诉讼。李骏硕从这些“露宿者”的角度拍摄了这部电影,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照。电影的主人公阿辉是一位“瘾君子”,妻子不知所踪,儿子早早去世,可以说是苟活于世。但在突遭暴力倾轧时,他没有选择退缩,而是用积极地抗争去赢得自己的尊严。
▲《浊水漂流》
阿辉将在街头认识的青年木仔视为自己的儿子,不但收留了这个从不开口讲话的流浪汉,还帮他完成了性启蒙。就在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木仔却被家人找到,原来他来自一个香港中产家庭,走失了八年,没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从伶牙俐齿变得不再说话。最终法院判决政府支付“露宿者”一人一笔赔偿却不道歉,失去了心灵依靠的阿辉决心以生命的代价反抗到底。
这部电影以真挚且勇敢的社会关怀博得了很多观众的好评,继承了香港电影的“平民精神”,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优质港片。李骏硕从一起真实事件入手为我们揭开了香港社会不为人知的现实一角,他通过对“露宿者”群像的塑造表达了自己对贫富差距等社会不公的控诉,其中木仔这个角色可以看作是年轻一代的自况,沉默在这部电影里被赋予了反抗的意味。
电影《一个人的葬礼》在“沉默”的层面表达得更加极致,全片只有一个角色,没有一句对白。黑白的电影以狗的视角展开,电影的镜头始终模仿着狗的行动,我们得以通过一种特殊的视角观察守林人老罗在父亲去世后如何独自举办葬礼的过程。
▲《一个人的葬礼》
因为失语,我们无法通过语言了解老罗,却感受到一种极致的孤独,老罗为父亲擦身体、穿寿衣,打棺材、挖坟墓……连贯的动作体现出他的能干,无声的哭泣展现出他的压抑。因为山上有狼,老罗失去了自己的小羊;在筋疲力尽之际,他决定放弃土葬,一把火为父亲举行了火葬。看到这里,观众的心情也低落到了极点,一个人如此努力地和各种困难搏斗,最终还是输给了环境。
这部作品的意义或许可以上升到哲学层面,但是由于缺乏社会背景的交代,也难免产生一种历史架空感,多少折损了电影的表达。当老罗最终还是选择将父亲火葬,他的绝望是溢出银幕的,这意味着放弃传统的为难,意味着和血亲历史的割断,意味着对暴力与不公的妥协?老罗没有表态,他始终无言。
缺席的父亲
一边是单身男性的失语,一边是父亲的缺席。“找爸爸”曾经是FIRST电影展的一个主题,据不完全统计,每年都会出现数部与寻找父亲有关的电影。父亲的形象对中国青年导演如此重要,他们不是极力书写父子/父女之间的和解,就是试图从精神的代父身上获得成长的力量,仿佛进入一种集体性的父亲缺席中,与上一代人的“弑父”情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背后的文化心态是值得分析的。
在今年电影展几乎所有关于家庭的电影中,父亲都是缺席的,家庭的秩序因此陷入混乱,这些电影不但没能借此对父权进行反思,反而在呼唤父亲的回归,仿佛只有男人成为真正的父亲,混乱的家庭才能重回正轨。这类电影在表达男性焦虑的同时,也展现出父权的衰落与阴影。
王晓丰导演的《老郑飞到天上去》恐怕是本届电影展最受争议的作品之一,该片原本在创投期间表现不错,还成功吸引到演员张颂文的加入,但是成片后效果不佳,口碑差强人意。
这部电影的故事核心并不复杂,讲述的是中年男人如何重塑自我的故事,甘肃小城,失业又失婚的老郑在少年亮亮的帮助下成了“网红”,他想利用这个身份找回失去的尊严,然而这个所谓维护城市文明秩序的“街道侠”迅速膨胀,开始以此发泄私愤。
不论以什么标准看,老郑都是一个失败的父亲,电影一开始,他的妻子就带走了孩子,他成为了失去父亲的亮亮精神意义的“父亲”。电影的最后,老郑用生命保护了亮亮,完成了作为父亲的使命。